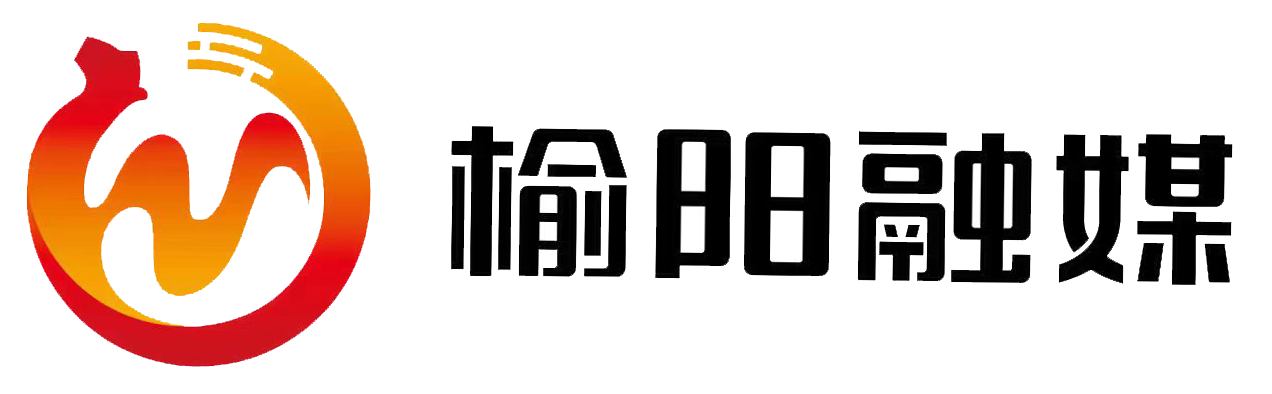1956年4月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国二文习字第6号),强调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遍调查工作,在已知不可移动文物和普查新发现文物基础上,由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并择其重要者报请国务院批准,置于国家保护之列,自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一普”)的序幕。
本文拟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围绕起止时间、成果统计、经验总结、性质辨析四个方面,对“一普”关键问题作简要探析,为深化当代中国文物普查史研究抛砖引玉。
1
关于“一普”起止时间
国务院《通知》并未明确规定“一普”的起止时间和标准时点,各省市普查工作启动与结束时间因此各不相同。
如山西省普查工作于1956年4月启动,江苏省普查工作于1956年8月启动,山东省普查工作于1956年10月启动、1957年6月结束,青海省普查工作于1957年3月启动,陕西省普查工作于1958年3月启动、11月结束,甘肃省普查工作于1958年4月启动,福建省普查工作于1958年4月启动、12月结束,湖南省普查工作于1958年6月启动、8月结束,浙江省普查工作于1958年8月启动,北京市普查工作于1959年10月结束,黑龙江、吉林等省普查工作持续至1960年上半年。吉林省于1960年9月23日至26日召开文物普查总结会,此后未见关于“一普”的后续报道。
故可推定“一普”于1956年4月初启动、1960年9月下旬基本结束,历时四年半。
2
关于“一普”成果统计
“一普”成果当时并未由国家层面统一发布。根据《文物参考资料》《文物》《考古通讯》等刊物所载文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1999)》及相关省市文物志记载,目前有普查成果存世的共17个省市。9个省市普查成果有分类统计,分别是:
北京市(寺庙2666座、古建筑616处、古墓葬700处、石刻3774处、革命遗址36处、古遗址51处、艺术文物124项、其他文物93项,合计8060处)。
上海市(寺庙46座、会馆公所19所、祠堂4处、古墓葬5座、石碑和石坊20处、传统民居300幢,合计394处)。
山东省(古遗址和革命旧址1008处、古墓葬4805处、古建筑863处、石刻1698处,合计8374处)。
山西省(古遗址420处、古墓葬513座、古建筑1043处、石刻1181处,合计3157处)。
河北省(古墓葬1330座、古遗址1005处、古建筑3937处,合计6272处)。
河南省(古遗址531处、古墓葬466座、古建筑570处、碑碣635通、石刻造像95处、革命旧址36处,合计2333处)。
江苏省(古遗址318处、古墓葬277座、古建筑136处、其他古迹312处,合计1043处)。
湖南省(古遗址217处、古墓葬573座、古建筑564处、石刻碑记178处、革命遗迹60处,合计1592处)。
陕西省(古遗址1188处、古墓葬3663座、石刻2771处、革命旧址20处,合计7642处)。
8个省(区)普查成果仅有不可移动文物总数量或部分类型文物数量,分别是:甘肃省(1000余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86处);安徽省(近1000处);福建省(2179处);浙江省(800余处);广东省(1191处);吉林省(古遗址和革命遗迹1023处);江西省(革命旧址和遗迹1523处)。
综上,根据现存“一普”成果资料统计,当时全国17个省(区、市)共调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47869处;其中14个省(市)不可移动文物数量超过千处,排名前五的文物大省(市)依次为:山东省、北京市、陕西省、河北省、山西省。
虽然此为不完全统计,只能大略勾勒“一普”成果之概貌,有的省份“一普”成果需待档案资料深入挖掘公布,但基于普查数据依然可以大致掌握当年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家底及分布总体情况,特别是传统文物大省(市)的“江湖地位”在60多年前即已基本排定座次。
需要指出的是,“一普”在各地的落实情况并不均衡,有的省(市)实现了普查全覆盖,有的省则只对文物资源富集地区进行普查,又如青海省普查工作主要集中于西宁、民和等传统农业区,对于牧业区则选取重点文物调查。
因此,完成“一普”工作的部分省份,其普查成果不一定全面完整地反映本省不可移动文物实际家底。
此外,“一普”的另一个成果是核定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普查工作逐步开展,至1956年底,全国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572处;至1957年底,全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至6726处;1959年,湖南省、青海省、上海市、山西省、江西省、江苏省先后公布共计142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一普”收官,全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达到8147处。还需要指出的是,“一普”启动之初各地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部分系根据地方志记载直接公布,经实地普查复核,从中挤出不少“水分”,在后续批次省保单位名录中进行了调整或重新公布。
3
关于“一普”经验总结
“一普”属于新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开创性的工作,各地在“省自为战”的同时,因地制宜摸索出了适合本地区实际的文物普查经验,既有共同点又各具特色。
首先是开展试点。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与山西省文化局合组文物普查试验工作队,于1956年4月初至5月底在晋南曲沃、闻喜、安邑、夏县、长治、高平、晋城7县开展试点,以期为全国文物普查取得经验,广东、河北、福建、浙江、湖北、陕西、江苏、山东、江西等省均派员参加试点工作。
此后,各省纷纷在本省开展普查试点,如湖北省试点为襄阳地区,江西省试点为上饶专区,河南省开封专区试点为荥阳县,江苏省试点为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常熟、苏州6市。
其次是培训干部。如山东省采取以会代训形式,河北、河南、陕西、湖北、福建等省通过举办文物讲习会或短期学习班,辅以田野调查实习,培训普查力量。
第三是发动群众,各地通过座谈会、展览等形式宣讲文物法令和普查政策;河北省在普查中访问60岁以上老农1100余人次,福建省南平专区普查队52天内召开群众座谈会199次,获得大量文物线索。
各省在“一普”中各有“高招”。有的省协调地方高校参与普查工作,广东省“一普”得到中科院广州分院、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的大力协助。吉林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57人,在指导教师带领下,协助省文管会和省博物馆赴磐石、敦化、农安等县开展以古遗址和东北抗联革命遗迹为重点的文物普查。
有的省普查记录档案质量较高,成为全国典型。辽宁省鞍山市按照历史艺术价值将千山风景区内28处古建筑分为甲乙丙丁四级,记录档案包括概述、历史沿革、现状、景物、平面图及照片;辽阳县普查发现的8处不可移动文物均详细绘制平面图和速写图并附有简要文字说明。吉林省四平专区行署每普查一地即填写记录表格并附地形草图和器物实测图。
有的省总结出接地气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之谈。山东省即墨县普查办归纳出“四边”(边宣传、边访问、边检查、边登记),“三勤”(腿勤、嘴勤、手勤),“两抓”(抓重点、抓发动)普查工作法。
河北省邯郸市普查组总结出“靠山找石窟、靠河找遗址”的经验和“三不”(不随便下结论、不粗枝大叶、不妨碍群众生产)的普查原则。
江苏省普查组结合江南地区自然环境,总结出“秋末至春初,草木枯萎,遗迹暴露地面,适宜做田野普查。
春夏、夏秋之交,不适宜田野普查,可作城市与名胜古迹调查”的经验。河北省唐山专区普查组亦指出,普查工作应注意季节性,以一、四季度为宜,春耕或夏收时节不便于古遗址墓葬调查,同时应尊重群众风俗习惯。
4
关于“一普”性质辨析
就狭义而言,根据国务院《通知》要求,“一普”对象主要是不可移动文物。但从现有资料考察,相关省份在实践中也顺便开展了可移动文物调查,许多地方还出现了群众踊跃上交和捐献可移动文物的现象。
“一普”过程中,陕西省收集陶器15万件、铜器6500余件、铁器3600余件、字画1000余件、革命文物1800余件、其他文物3万余件;吉林省征集和采集可移动文物7480件,其中较完好者700余件;山东省发现书画、陶瓷、铜器23066件;山西省征集革命文物236件;广东省征集革命文物326件;河北省征集可移动文物12967件;湖南省征集可移动文物14620件。
这些可移动文物作为“一普”的副产品抑或意外收获,为各省建立博物馆(纪念馆)提供了一定藏品基础。
此外,“一普”并非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唯一的文物普查项目,当时与其同步开展的还有相关省份的常态化革命文物普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专项文物普查,如文物部门配合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对南北疆相关古遗址、古城址、冶铁遗址、岩画、石刻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过普查并征集可移动文物2973件,浙江省文管会对畲族群众聚居区的民俗文物和革命文物进行过专项调查。
这些文物普查工作与“一普”在时间段上相互重合交织,有的单独实施,有的成为“一普”组成部分,彼此是否存在成果共享仍需考证。
可以说,“一普”是以不可移动文物调查登录为主、可移动文物调查征集为辅的综合性文物普查。
就广义而言,“一普”延续和巩固了自晚清以降由中央政府组织开展文物普查这一国家文化责任,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意义。
它不仅仅是常规的国情国力调查抑或文物保护基础工作,在当时还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推动了基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体系成型。
吉林省通过“一普”,初步完善了有保护范围、有记录档案、有保护标志、有人管理的“四有”制度,建立文物档案951份、树立文物保护牌655个、组建群众性文物保护小组484个、聘请文物通讯员557名。福建省南平专区文物普查队协助各县建立文管会33个、文物保护小组165个。
二是为思想交流甚至是“红脸出汗”的观点争鸣提供了平台,上至省政府领导下至基层普查人员,围绕热点畅所欲言,对于文物普查相关理念性、原则性、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既统一了思想认识,又曝光了问题和不足。时任山东省副省长余修在全省第一次文物工作会议上针对什么是文物?文物有什么作用?如何保护文物等干部群众关切的问题作了阐述,同时用生动的语言指出,之所以搞文物普查就是为了使文物古迹“物各有主、插标为记”,确保文物安全。
罗容曾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谈文物古迹的普查工作》一文,各省普查工作者随后刊发多篇商榷文章,罗容亦发表三点声明,对原观点进行修正:一是并非所有调查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都应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而是应该经过严格遴选与核定;二是文物保护单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全民财产之提法不够严谨,因为某些地区的某些文物保护单位产权可能属于私有,实践中不宜“一刀切”;三是许多地区受限于人员、技术、经费、时间等因素,难以达到作者提出的理想化的普查高标准,应该实事求是,满足普查基本要求即可。
广东省汕头、惠阳专区文物普查队成员区家法以切身体会指出,协助普查工作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同学已受过考古专业训练,尚且不能完全胜任古建筑普查工作;而有的省份普查人员仅仅受过几天短训就上岗,更难以保证普查质量,因此提出普查工作要正确处理“快”与“好”的关系。
湖北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更坦言称,普查干部短期培训班在教学时间、师资选配、教材准备等方面均需慎重考虑和研究,否则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总而言之,虽然“一普”成果不够全面和精确,在组织实施方面存在若干短板,在普查技术方面亦无法与此后历次文物普查同日而语,但其影响深远,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领域奠基工程的历史地位应予客观评价。
“四普”全面启动之际,重温“一普”往事特别是文物普查前辈筚路蓝缕的拓荒之功确有必要,相关经验对于我们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四普”不无裨益,而那些能够反映包括“一普”在内的新中国早期文物保护管理历程的遗迹和物证,亦应成为“四普”以至未来可移动文物“二普”的重要普查对象。